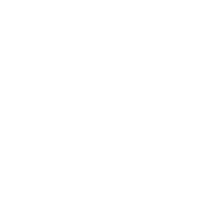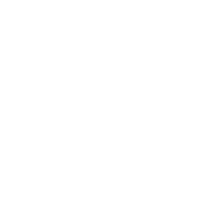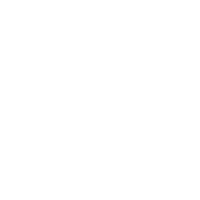工傷論文
追繳社保的勞動監察時效適用實踐與思考
摘要
一直以來,無論是在理論探討中還是在執法實踐中,社會保險費的追究時效都是一個頭疼且富有爭議的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規定的不明確以及理論界對這個問題認識的偏差。筆者作為 一名一線勞動保障監察員,也深受這個問題的困擾。本文先闡述勞動監察時效的性質,隨后探討為什么社會保險費的追繳應當適用勞動監察時效。同時,結合筆者承辦的四個典型社會保險費投訴案例,解讀當前執法實踐中追繳社會保險費的時效適用問題及存在的爭議,以期減少對這一問題的困惑。
一、勞動監察時效的性質
《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是關于勞動違法行為的追究時效規定。
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則的行為在2年內未被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發現,也未被舉報、投訴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不再查處。
前款規定的期限,自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則的行為發生之日起計算;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
所謂時效,一般是指法律關于刑事責任、民事訴訟權利等的有效期限。具體到勞動法領域,也就是關于勞動者請求保護其權利的有效期限。根據勞動者權利救濟的途徑,可以將勞動法領域的時效劃分為勞動監察時效和勞動仲裁時效。因而,從勞動者的視角來看,勞動監察時效是勞動者向勞動監察機構舉報投訴的有效期限;從執法部門的視角來說,勞動監察時效是勞動監察機構對用人單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行為責任追究的法定期限。
1、勞動監察時效與訴訟時效的區別
實踐中,有人會將勞動監察時效與訴訟時效的概念混同。兩者確實有相似的部分,即都是在一定期限內未履行請求職能部門(法院或勞動部門)保護其權利而喪失公力救濟。然而訴訟時效一般指的是民法上的概念,即權利人在法定期間內怠于履行請求權,在期間屆滿后,其請求法院保護其民事權利的權利歸于消滅的制度。兩者所處的領域不同,兩者尋求公力救濟的職能部門也不同。同時,訴訟時效有中止、中斷情形,而勞動監察時效的兩年是不變期間。因而,從權利保護期間是否固定的角度來看,勞動監察時效更接近民法學理上“除斥期間”的概念。
2、勞動監察時效與仲裁時效的區別
勞動監察時效與勞動仲裁時效均為勞動法領域內的時效制度,然而兩者也有著諸多區別。首先,兩種時效長短不同。勞動監察時效為2年,而勞動仲裁中一般時效為1年。其次,兩種時效起訴點不同。勞動監察時效是自違法行為發生其計算,違法行為連續的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而仲裁時效自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最后,有無中止中斷情形不同。勞動監察時效是不變時效,無中止中斷情形;勞動仲裁時效有中止中斷情形,因而勞動仲裁時效類似于訴訟時效的概念,可以視為勞動法領域的“訴訟時效”。
如果一定要類比的話,筆者認為勞動監察時效從性質上看最接近“刑事追訴時效”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勞動監察時效視為勞動法領域的“追訴時效”。因而,可以將勞動監察時效稱為“勞動監察追究時效”或者“勞動監察受理時效”,本文中統稱為“勞動監察時效”。
二、社會保險費追繳該不該適用勞動監察時效
【案例1】 2015年2月27日,上海市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收到李某郵遞過來的舉報材料。據李某所述,自2002年10月起李某開始在J學校擔任門衛保安,期間用人單位主體多次變更,自2011年4月起與Z物業公司建立勞動關系,由Z物業公司派遣至J學校工作。李某于2014年9月向浦東新區仲裁委員會就勞務派遣合同糾紛提起仲裁,庭審期間,李某又要求確認與Z物業公司自2011年4月至2012年8月期間的勞動關系。因庭審中Z物業公司對此予以確認,浦東新區仲裁委遂在裁決書中對李某與Z物業公司在2011年4月至2012年8月期間的勞動關系予以確認。李某在舉報材料中要求上海Z物業有限公司為其繳納2011年4月至2012年8的社會保險費。
本案即為典型的社會保險費追繳時效適用問題。目前的執法實踐中,勞動監察機構普遍認為社會保險費追繳應當與其他違法行為一樣,受到兩年的勞動監察時效約束。本案中李某于2015年2月27日提出投訴,要求勞動監察機構責令Z物業公司為其補繳2011年4月至2012年8月期間的社會保險費。很顯然,提出投訴的時間已經超過了違法行為終了之日起2年,因而李某的投訴勞動監察機構并未受理。 2015年2月28日,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電話答復李某來信已收悉,因已超過勞動監察兩年時效而不予處理。隨后,根據李某要求,向其郵遞書面不予受理決定書。
然而,理論界對此頗有爭議,認為社會保險費的追繳不應當受制于時效規定。筆者認為,無論是從法律的角度,還是基于現實的考量,社會保險費追繳都應該適用勞動監察時效規定。
1、社會保險法不能成為社保追繳豁免時效的依據
很多人認為,《社會保險法》中并無追繳時效的規定,作為上位法的《社會保險法》效力要高于法規《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因而社會保險費的追繳問題不應該受制于勞動監察時效約束,這也是持此觀點的主要依據之一。
縱觀《社會保險法》全文,確實沒有涉及社會保險費追繳的時效或者年限規定。然而,僅僅是沒有涉及社保費追繳的時效規定,卻并不能理解為否定社會保險費的追繳適用勞動監察時效。沒有規定與否認規定完全是兩回事。此時,作為上位法的《社會保險法》與《勞動保障監察條例》中的時效規定并無沖突,完全不能成為社保追繳行為可以豁免勞動監察時效的依據。
2、對違法行為的追究設置時效規定是通行做法
法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因而任何違法行為都是對國家意志的違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違法行為都侵犯了國家利益(意志不得違背的利益),因而拖欠工資等其他違法行為都侵犯了國家利益,那么對社會保險費追繳的行為又為何可以單單豁免呢?此時,持反對論者可能會辯稱社會保險費追繳行為涉及到國家的實體利益,也即是社會保險基金賬戶中的真金白銀。然而實踐中,作為社會保險費事務的具體經辦部門社保中心對主動的社會補繳行為也顯得非常審慎。以上海地區為例,用人單位主動補繳勞動者6個月以內的社會保險費,可以很方便的通過網上自助經辦平臺或者窗口補繳,但是對于補繳6個月之前的社會保險費的辦理要求則非常苛刻,以至于很多情況下即便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均愿意補繳實踐中也無法辦理補繳手續。由此可見,社保費補繳并非多多益善,也非單純的牽涉國家利益,否則就應該多鼓勵對社保歷史欠賬主動補繳行為。再比如,違反刑法的行為客觀上比未繳納社會保險費行為有著更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性,然而即便是故意殺人這樣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暴力犯罪行為,刑法依然設置了追訴時效,通常在二十年內未被發現則不再追訴。因而,對社保違法行為的追究設置時效符合對違反行為糾正的通行做法。
3、追繳社保費適用時效規定是基于現實的考量
對任何違法行為的糾正都存在著現實的成本,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違法行為糾正的成本會逐步上升,因而設置追究時效是基于現實成本的考量。以案例1為例,倘若勞動監察機構受理李某投訴,那么按照規定,需要調取Z物業公司2011年4月至2012年8月期間的工資單。然而《工資支付暫行規定》對于用人單位工資發放記錄的要求僅僅是保存兩年以上備查(參見《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第六條),也即是用人單位保存書面公司發放記錄的法定義務即為兩年。實踐中用人單位保存三四年前的工資發放記錄,特別是對于中小微企業來說,更無現實的可能。大量的公司工資發放并不那么規范,公司的財務憑證也沒有相應記錄。在2015年2月27日以后,要求Z物業公司提供2011年4月至2012年8月期間的工資發放記錄既無法律上的依據,很大程度上也無現實的可能性。在工資金額都無法確認的情況下,社保補繳的基數也就無法確認,自然也就難以作出要求用人單位補繳社保的具體行政行為。綜上,追繳社保費行為適用勞動監察時效規定也是基于現實的考量。
三、追繳社會保險費如何適用勞動監察時效
1、違法行為終了之日起兩年內提起投訴是受理前提
案例1中,上海市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于2015年2月27日收到李某郵遞過來的舉報材料,要求Z物業公司為其繳納2011年4月至2012年8月的社會保險費。根據勞動監察時效規定,違法行為連續的,從行為終了之日起算時效,因而李某應當在自2012年8月起兩年內(最晚于2014年8月)提起投訴。李某向勞動監察機構提起投訴的日期為2015年2月,因而已超過兩年時效。同時,需要調查在2014年8月之前,李某是否曾就其社保問題曾向任一勞動保障機構提出過投訴或者舉報即可。據此,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在勞動保障監察系統中檢索了Z物業公司的勞動監察案件歷史記錄,未發曾有該違法行為的投訴或舉報案件,因而李某的投訴請求不予受理。
2、社保漏繳行為在時效內可追繳至違法行為起始日期
【案例2】 2016年1月17日,熊某來到上海市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投訴上海J保潔公司未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經查,投訴人熊某自2012年1月開始在J保潔公司擔任保潔員,于2016年1月25日離職。J保潔公司始終未繳納熊某在職期間的社會保險費。現熊某要求J保潔公司為其補繳2012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間的社會保險費。
因為社保漏繳期間,整個違法行為始終處于連續狀態,因而時效起算點應自違法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如果在時效范圍內,那么整個違法行為都應當視為在時效范圍內,也都應該被糾正。具體到本案,2016年4月11日,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責令J保潔公司限期整改,補繳投訴人熊某2012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間的社會保險費。2016年5月7日,J保潔公司補繳了熊某2012年1月至2016年1月的社會保險費。
3、社保少繳行為在適用時效時的爭議
【案例3】2016年7月22日,鮑某來到上海市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投訴Y投資公司未按規定繳納其社會保險費。經查,投訴人鮑某于2009年9月1日開始在Y投資公司工作,該單位自鮑某入職起便為其繳納了社會保險費,但由于歷史原因,始終按照最低繳納基數。現投訴人鮑某要求Y公司為其繳納2009年9月至2016年7月期間的社會保險差額部分。
關于未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的違法行為,除了常規的漏繳行為,還包括少繳行為,即繳納了社會保險費但是繳納的基數低于實際工資水平。一般來說,在執法實踐中將社保漏繳行為視為違法行為連續,因而在追究時可以追繳至違法行為起始日期。然而對于社保少繳行為是否視為違法行為連續或者繼續,既無明文規定,也無統一的執行口徑,導致執法實踐中操作不一。
一種觀點認為,社保少繳行為中每個月的社會保險費低于法定基數都是獨立的違法行為,社保少繳行為即便一直存在也不視為違法行為狀態處于連續,因而在適用時效時以2年為界,在2年時效范圍內的期限予以處理,超過2年的少繳行為則不予處理。類似于仲裁實踐中,將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所需支付的雙倍工資性質界定為賠償金而非工資,因而適用一般時效的情形。
另一種觀點認為,社保少繳行為與社保漏繳行為性質類似,對于一直存在的少繳行為應當視為違法行為持續,適用時效時以違法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判定少繳行為在時效范圍內,則此時與社保漏繳行為的適用時效問題并無差別,可以一直追繳到少繳行為的起始日期。
實踐中,還存在一種折中的操作,也就是考慮到少繳行為相對較輕的違法性質及較為普遍的狀況,而將兩種觀點折中結合起來。這種折中的操作實踐,在判定違法行為是否在時效范圍內時采取觀點二,也即是將社保少繳行為視為違法行為狀態聯系;在違法行為被判定為時效范圍內時,就追繳年限的問題上采用觀點一,也即是社保少繳行為的追繳上限為2年。
具體到案例3中,承辦機構采取的就是折中觀點的操作實踐。2016年9月12日,上海市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責令Y投資工資限期整改,補繳投訴人鮑某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間的社會保險費差額部分。2016年9月27日,Y投資公司補繳了鮑某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間的社會保險費差額89990.4元。
4、社保漏繳行為與少繳行為是否為同一種違法行為
【案例4】2016年3月23日,孟某來到上海市勞動保障監察總隊投訴上海P電信公司未按規定繳納其社會保險費。經查,孟某于2010年10月入職P公司,于2015年9月離職。期間,P公司于2012年10月開始為其繳納社保,但此時并未按照孟某實際工資作為繳納基數;P公司于2014年4開始按照孟某實際工資水平作為繳納基數。
現孟某投訴事項為:1、要求P公司補繳2010年10月至2012年8月社保(未繳);2、要求P公司補繳2012年9月至2014年3月社保差額(少繳)。
本案流轉至上海市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承辦。
本案爭議頗大,在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疑難案件討論會上也引起了強烈的爭議。對于投訴請求2都持支持觀點,但對于投訴請求1是否應支持有著卻有著截然相反的觀點。
(1)社保未繳與少繳系相同違法行為
社保未繳與少繳都屬于“未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在勞動監察機構在執法實踐中,兩種行為也系同一個案由,也即是“未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同時,在責令整改通知書或行政處理決定書中,兩種行為的違法依據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七十二條。因此,兩種行為的表現形式雖然有所不同,但從案由以及執法實踐中認定違法依據的角度,兩者卻并無任何差別。兩種行為都屬于未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勞動者現主張P 公司自2010年10月至2014年3月始終未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那么從這個角度看違法行為處于連續狀態,自然未繳的違法行為也落在時效范圍內。
(2)社保未繳與少繳系不同違法行為
無論是從違法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還是從一般勞動者的客觀認知來看,社保未繳與少繳都有著本質的區別。雖然兩種違法行為都屬于“未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同一個案由,然而屬于同一案由下兩種不同的細分違法行為,或者說“未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是社保未繳和少繳兩種行為的上位概念。正如拖欠工資和未繳納社會保險費的行為都可以稱之為“違反勞動法的行為”一樣,不能因為其有著共同的上位概念,而將兩種行為視為同一行為。
因而,漏繳行為和少繳行為是相互獨立的,P公司于2012年10月開始為孟某繳納社會保險費而導致違法行為一在2012年10月終了,自然孟某的投訴事項1自2014年10月就已過了監察時效。
兩種觀點截然相反,筆者同意觀點二,也即是社保未繳納與少繳系不同違法行為。
具體原因如下:
(1)表現形式不同。
社保未繳是沒有繳納,而社保少繳的前提是已經繳納了社保,是否繳納有著本質的區別,這種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也是所有人可以感知到的,兩種行為的表現形式完全不同。
(2)違法依據不同
雖然兩種行為均屬于“未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這一相同案由下的行為,且實踐中勞動監察機構作出責令整改的已經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七十二條,然而筆者認為對于社保少繳行為以七十二條作為整改依據是值得商榷的,或者說是無奈之舉。《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七十二條:
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
我們仔細看下七十二條,其實七十二僅僅規定用人單位應該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并不涉及社保繳費的基數。因而,違法行為一的違法依據在七十二條沒有問題,然而對于社保少繳行為的違法依據為七十二條其實是非常牽強的。關于社保的繳費基數的規定在《關于確定繳納社會保險費工資基數的通知》中“當年個人繳費基數按職工本人上年月平均工資性收入確定。”由此可見,實際上兩種行為的違法依據并不相同,只是《關于確定繳納社會保險費工資基數的通知》是規范性文件,并不能作為行政處理的依據。
綜上所述,從行為的表現形式和實質的違法依據,兩種行為均不相同,因而不能認定社保未繳和少繳系同一樣違法行為。具體到本案中,2010年10月至2012年9月社保未繳納的違法行為在2012年10月就已終了,孟某應當在2014年10月前向勞動監察機構提起投訴方才在時效范圍內。
文:夏小偉,上海市靜安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中國勞動》2017年第3期。





 冀公網安備13010202003181號
冀公網安備13010202003181號